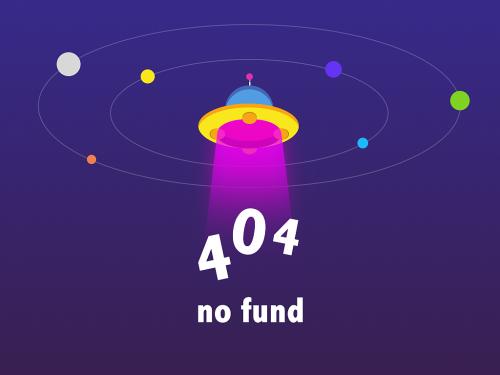□关立蓉
打开车门,踏上这块土地的刹那间,凛冽的风,裹挟着大海的气息,呼啸着吹来,脸上裸露的皮肤,猛地一紧,似有刀割。不由得把衣服裹紧些,心里惊叹,到底是海边的风啊!
今年春节,终于回到故乡。我们一家三口,决定去海边走走。繁华城市长大的女儿,年年岁岁,吃着外婆捎来的海鲜:文蛤、泥螺、竹蛏、鲳鱼……而对南黄海的波澜壮阔,却是一个模糊的印记。这个特殊的日子,来到海边,感恩大海的馈赠,完成内心升腾已久的心愿。
站在巨石垒成的堤坝之上,坚实的水泥围栏之外,便是声名远扬的刘埠渔港。港湾内碧绿的水波,轻轻晃动,和远方浩渺的大海,完全是两个世界。正月初一,辛勤的渔民们仍旧出海。
此刻,这个现代化的渔港里,紧紧挨挨,停泊着近百艘渔船,桅樯林立,红旗猎猎。大部分渔船钢铁铸成,身宽体阔,气势汹涌。间或几条体态小巧的木质渔船,海水经年的浸泡,船身已成深褐色,一道道沧桑的痕迹,证明了它一段又一段艰辛的旅程。远处,又一艘渔船驶来,浪花飞溅,一个灵巧的转弯,稳稳入港。港口外闸门,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缓缓闭合。
一阵加大分贝的“哒哒”声,骤然响起,我们沿着栏杆,循声向西奔去,内闸门前, 三个小舢板开动马达,平静的水面顿时翻滚起朵朵浪花。
小舢板之后,靠近围栏,停泊着一艘体型庞大的钢质船,船身足有10多米长。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渔民,穿件厚实的棉大衣站立在船首,黑红黑红的脸庞,浓眉之下的一双大眼炯炯有神。他的神情昂然严肃,仿佛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,目视前方。银白色的闸门,足有两层楼房高,在阳光照耀下,反射着瑰丽的光芒。甲板上,竖立着半人多高的巨型鞭炮,鲜艳的红色包装彩带,迎风飘扬。
风浪在船体上留下了划痕和纹路。那些灰黑色的伤痕是多年前礁石撞击留下的痕迹吗?伤痕表面涂过一层蜡,阳光将蜡烤干,痕迹停留在上边,让我想象它与风浪搏击的姿势。那些黄褐色的斑痕是前进的代价,每冲过一个浪头,它们就经历一些震荡。还有一些凹纹,它们熟悉海水的旋涡,宛若谛听水声的耳朵……
“开闸么?”
“再等会!”
小巧的舢板,在波浪中上下沉浮,三位渔民,稳稳地坐在舢板横杆之上,中间的一位竟然没有握住方向盘,靠脚下用力保持平衡,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,点燃,吐出一口口烟圈,他的手指上有枚硕大的金戒指。
“他们在附近养紫菜,下晚点就回来。我们这一趟出去,最起码要10天8天的……”和我搭话的渔民,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。
“开了!开了!”听得一声欢呼。如洞天石扉,訇然中开,闸门缓缓露出一条窄缝,海水卷着浪花,争先恐后地涌了进来,闸门向两边推进,海水奔腾着汹涌而下,渐渐地,闸内外的水面齐平,三个小舢板滑过波浪,如三羽翎毛飘落闸外。
闸门完全打开,海水在灿烂的阳光下奔涌,在凛冽的寒风中欢畅,卷起千堆雪,触摸着港湾内的每一艘船,把大海的气息,大海的豪迈,传递给每一位整装待发的渔民。
机声隆隆,紧一阵,猛一阵,盖过风的怒吼。威武的大船,驶向港闸。中年渔民点燃了鞭炮,爆炸声响彻云霄。弥漫的烟雾中,拇指粗的缆绳沾满了海草的浮筒、泛着青绿的渔网,像慢镜头从眼前划过。一副闪着金属光泽的铁锚,静静俯卧在甲板上,颜色那样鲜亮,海水浸润抚摸它长长短短的尖角,在它的生命中,经历过多少次出海远航?船尾,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渔民正在仔细地清理一棵黑塌菜,抖落泥土,择去枯叶。旁边,放着十几桶大号矿泉水。船舱的门上,贴着鲜红的春联,挂着腊肉、香肠……
1、2、3、4……我在心里默默数着,注视着一艘艘渔船,如列队整齐的卫士,依次通过闸门,有人放起烟花,水面上升起夺目的绚烂。最后一艘船顺利通过闸门,闸门缓缓关闭。整个渔港恢复了寂静。我们向远方眺望,船队已经驶向大海深处,只能看到它们越来越模糊、越来越小的背影。“白浪茫茫与海连,平沙浩浩四无边。”
几只海鸥在渔港上空飞翔,划出优美的弧线,它们的腹部如雪般晶莹洁白,畅快的鸣叫声,声声悦耳。一个旋转,它们向浩瀚的大海飞去,是去追赶远去的船队吧!多么渴望,也生出一双海鸟的翅膀,随船前往,去倾听大海奏起的深沉雄浑的乐章,去体验渔民辛勤的劳作,分享丰收的喜悦。